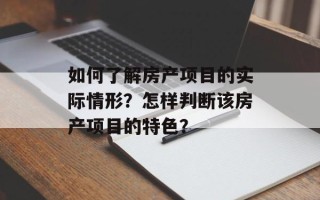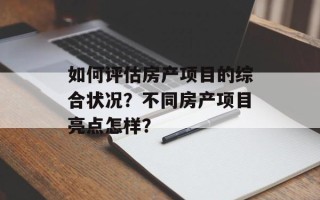编者按1 *** 5年1月4日,《京报副刊》在孙伏园的主持下,发布《一 *** 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》:“青年爱读书十部”和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。一时名流,如胡适、梁启超、周作人、马裕藻、 *** 、林语堂、沈兼士、顾颉刚、汪兆铭、马叙伦、罗庸、许寿裳、太虚等78人,先后参与推荐必读书。特别是因为大文豪、思想文化界斗士 *** 交了“白卷”,坦言“从来没有留心过,所以现在说不出”,并在“附注”栏说明道,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 *** 书,多看外国书”,引发思想文化界的激烈争论,衍化为近代文化史上的 *** 。此次事件,是当时声势盛大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在大众阅读层面的辐射。它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在治学领域、兴趣、理路和 *** 等方面的差异,还因其关乎“改造 *** *** ”“再造文明”“民族国家认同”乃至“救亡图存”等与时势相关的重大问题,呈现了他们对中与西、传统与现代、启蒙与救亡等关系的不同思考。衍至今日,这些问题仍是困扰我们、需要我们直面的,先贤的思考无疑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。值此事件发生一百周年之际,特推此文,以为纪念。
梁启超推荐国学书目的“晚年定论”
文丨陈斐
多年执教、一生以启蒙为职志的近代思想文化界领袖梁启超,著述之余,也编纂过不少接引后学、指点门径的书目及读书指导类著作。目前,学界关注较为集中的是他与胡适论战的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(1 *** 3),对其早年所编《读书分月课程》( *** 4)《西书提要》《西学书目表》( *** 6)《东籍月旦》(1902)及晚年所编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(1 *** 3)《读书示例——〈荀子〉》(1 *** 5)等也时有论及,唯独对其堪称“晚年定论”,更具逻辑 *** 且周详、 *** 的《读书法讲义》(下文简称“《读书法》”)罕见提及,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。这可能与此著未收入《饮冰室合集》有很大关系。《读书法》系商务函授学社国文科初级教材,成书时间比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晚四五个月。一年多之后,梁启超应邀推荐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(详下),即沿着《读书法》的思路及框架筛选[1],足见其为任公“晚年定论”。
展开全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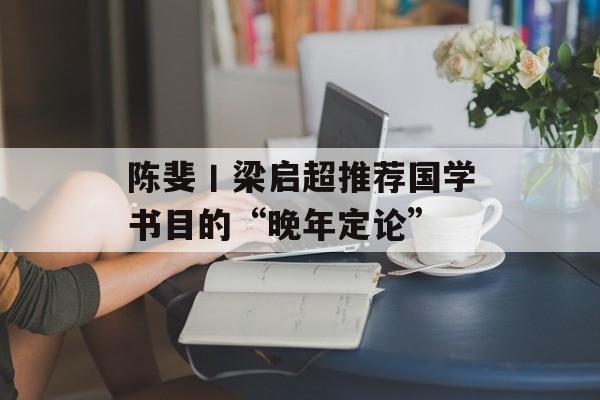
《读书法》系梁启超1 *** 3年 *** 月间,应商务高管高梦旦约稿而撰。梁氏书札对此有清晰呈现,其1 *** 3年7月31日《致菊梦两公书》云:“梦兄前惠书,因彼时方从西山返天津,放在行箧中,遂忘作答,荒唐极了。续接菊兄书……梦兄委撰《读书法》,极愿从事,惟因一月来在南开演讲,带编讲义,日不暇给,故未尝着手。顷南开讲义将完,而教育改进社又将开会,须入京旬日,大约八月杪九月初始能属稿,不审太迟否(又尚有一题系何题,请并示)。若尚可赶及,当暂阁置一切即成之。”8月11日《与菊生、梦旦两兄书》曰:“书悉。国学讲义中《读书法》一种,顷已撰成一半,因恐全讲义出版期迫,谨先寄上。今夕到北戴河小憩,约五六日便归,余半当在彼成之。”9月15日《致菊公书》言:“一月前寄上《读书法》前半篇,未得复书,不知有无失落,祈一见示。后半篇近数日始续成,因钞胥乏人,明日入京当先钞上。下半年在清华讲学。”[2]可见,商务方面当时还拟约请梁启超另撰一种,但不知何故,并未落实。国文科最后成书的讲义中,梁氏所撰仅有《读书法》。
联系当时的社会、文化背景可知,《读书法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颇大的文化事件国学书目推荐之产物。1 *** 3年2月,应将要赴美留学的胡敦元等四个清华 *** 的请求,胡适“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 *** 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”[3],开列出《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,初刊于《东方 *** 》第20卷第4号(1 *** 3年2月25日),再刊于《努力周报》增刊《读书 *** 》第7期(1 *** 3年3月4日),引起不少人关注。3月11日,《清华周刊》记者致信胡适质疑,胡适随后作复[4]。该刊记者还约请梁启超另拟,在京郊休假的梁氏于4月26日“凭忆想”撰成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,初刊于《清华周刊·书报介绍副镌》第3期(1 *** 3年5月4日),发表时另附梁氏所撰《更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《治国学杂话》《评胡适之的〈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〉》三文。“梁、胡所拟者,以盛名为之辅,乃不胫而走,坊间汇订之书目,闻亦销行巨万”(曹聚仁《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》)[5]。在他们的影响下,相关商榷讨论及另拟书目纷纷 *** [6],如李笠撰有《国学用书撰要》,附录《评胡适书目》和《评梁启超书目》[7]。梁启超本人亦应商务约稿,改写出更为 *** 周密的《读书法》,先以“读书法”为题,连载于《清华周刊·书报介绍副镌》第5期[8](1 *** 3年9月29日)和第7期(12月2日),后又由商务推出单行本。1 *** 5年1月4日,《京报副刊》在孙伏园的主持下,发布《一 *** 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》:“青年爱读书十部”和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。关于后者,启事提到:“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,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。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,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。”随后,该报从2月11日至4月9日,共登出78人推荐的必读书目,除胡适、梁启超再度亮相外,还有周作人、马裕藻、 *** 、林语堂、沈兼士、顾颉刚、汪兆铭、马叙伦、罗庸、许寿裳、太虚等名流参与。整体来看,诸人推荐的“青年必读书”和青年自己票选的“爱读书”中,中国古籍或时人撰著的国学研究论著占绝对优势[9]。因此,这次征求活动可视为胡、梁引发的国学书目推荐事件的持续“发酵”。然而,大文豪、思想文化界斗士 *** 却交了“白卷”,坦言“从来没有留心过,所以现在说不出”,并在“附注”栏说明道: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 *** 书,多看外国书。”[10]此言一出,更是引来一番关于要不要“读中国书”的激烈争论。
《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特刊》公布的票选结果:青年爱读书书目,前十种为:《红楼梦》183、《 *** 》100、《西厢》75、《呐喊》69、《史记》68、《三国志》62、《儒林外史》57、《诗经》57、《左传》56、《胡适文存》51
国学书目推荐事件是当时声势盛大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在大众阅读层面的辐射。它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在治学领域、兴趣、理路和 *** 等方面的差异,还因其关乎“改造 *** *** ”“再造文明”“民族国家认同”乃至“救亡图存”等与时势相关的重大问题,呈现了他们对中与西、传统与现代、启蒙与救亡等关系的不同思考。事件的核心人物胡适、梁启超、 *** 所持主张颇有 *** *** 。
胡适乃“新文化运动”健将。1919年12月,他发表《新 *** 的意义》一文,正式提出“研究问题,输入学理,整理国故,再造文明”的十六字方针,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。胡适主张以“评判的态度,科学的精神,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”[11],把杂乱无序的“国故”改造为成 *** 且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。《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即其“整理国故”理念、 *** 乃至着力点的反映或实践。此目分工具、思想史、文学史三部,每部下的书籍大致按内容及成书先后顺序排列,书后附有注释说明版本、价值、用途或读法等。思想史、文学史两部,恰好是胡适从事国故整理与研究的着力点,他也将其视为“国学更低限度”。文学史书目基本遵照他扩大研究范围,重视白话和民间文学的理念,有意勾勒了一条话本小说和戏曲的发展脉络。思想史书目首列其自著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随后所列先秦之书及次序亦基本与此书一致,而藉秦以下书目,则可以窥测此书未成部分的概貌。此外,胡适刻意提点青年“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 *** ,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”[12],并开列自己的《章实斋年谱》和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等时人论著,提倡青年阅读经过整理的古书……凡此,意在引导青年体会他所倡导的“历史的眼光”“ *** 的整理”(胡适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)等“整理国故”理路[13],期望授人以渔,教给青年“历史的国学研究法”[14]。不过,随着“整理国故”运动越来越沉溺于发扬国光,身为“新文化运动”领袖的胡适又转 *** 度,公开感叹“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,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”,“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”[15],认为中国旧籍“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”,青年人要少读,应多读外国书[16],“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”[17]。
胡适
*** 本人对国故颇有兴趣,喜好汉画像拓片,大量购买碑帖、墓志,著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也盛赞过胡适《 *** 续集两种·序》等古代小说考证成果[18]。私下里, *** 亦开列过国学方面的书单。然而,《京报副刊》的“青年必读书”征求属于公众媒体事件, *** 非常清楚此事件及他本人的巨大影响力。他对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兴起后,思想界乃至全社会愈来愈浓厚的埋头读古书风气非常不满,担心“尊孔复古”的逆流死灰复燃。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推荐,且有把“青年必读书”弄成“青年必读国学书”的势头时, *** 终于忍不住以极端的“交白卷”形式表明态度: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 *** 书,多看外国书”,力图以此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国家民族希望的青年人的思想走向。在 *** 看来,身处国家民族危机深重、现代化远未完成的时代,应该倡导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现实,而不是拿“整理国故”的旗子号召他们像老先生一样“埋在南窗下读死书”,“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”[19];“我 *** 书时,总觉得就沉静下去,与实人生离开;读外国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书时,往往就与人生接触,想做点事。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,也多是僵 *** 的乐观;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,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……少 *** 书,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‘行’,不是‘言’”[20];“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,是:一要生存,二要温饱,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,无论是古是今,是人是 *** ,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,百宋千元,天球河图,金人玉佛,祖传丸散,秘制膏丹,全都踏倒他。”[21]这个主张和胡适在“整理国故”后期的看法一致,只不过 *** 的文化嗅觉和洞察力更为敏锐、超前。
***
至于梁启超,“戊戌维新”失败后, *** 思路由自上而下的 *** 改良转向自下而上的思想启蒙,愈来愈意识到救国首在“新民”,对“ *** 常识”的培养十分重视。1910年,他曾谋划发起“ *** 常识学会”,打算联络同人编纂《 *** 常识讲义》《 *** 常识小丛书》和《 *** 常识丛书》,用为会员函授教材或廉价发售的普及读物。梁启超拟定的《 *** 常识讲义》科目中,即有“读书法”。次年,他还就这些书籍印售事宜,和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反复磋商,张不看好《 *** 常识讲义》,但乐意承担《 *** 常识丛书》,并建议补入科学内容。尽管上述成立学会、编印书籍的系列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,但为商务成功约请梁启超撰写《读书法》做了铺垫。
夏晓虹指出,梁启超对“ *** 常识”教育的构想与实践,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。发起“ *** 常识学会”时,由于此会是应筹备立宪而起,以培养合格的立宪 *** 为目标,故梁启超强调给社会中坚的中年人“采补”其最为欠缺但又关系国家体制与命脉的西方现代 *** 、法律与经济知识。1 *** 0年“欧游”后,经由对“一战”后西方精神危机的切近体察,梁启超重新确立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充足自信。此时,随着他的人生由 *** 从政转向以学术著述与高校讲学为主,梁启超“ *** 常识”教育的施教对象也向青年 *** 倾斜,内容亦偏重人文学科、重视人格修养,最终更集聚到国学,倡导“德 *** 的学问”与“文献的学问”并重[22]。
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《读书法》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等,即是“维新巨子梁启超从一个热烈追慕西方现代文明的盗火者,而变成了一个审择反思西方现代 *** 并阐扬昌明本土精神价值”[23],会通中西而创造一种“新文化”以贡献于人类的思想者后,“淬厉”传统以普及“ *** 常识”的具体实践。
梁启超
梁启超、胡适二人所开国学书目,诚如夏晓虹所言,体现了“常识”与“专门学识”观念的冲突。梁启超《评胡适之的〈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〉》对胡适的批评,即主要着眼于此。他指责胡目一方面“博而寡要”,主观 *** 太强,胡适“正在做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文学史,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”,“忘却 *** 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,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。试问连《史记》没有读过的人,读崔适《史记探源》懂他说的什么”,且“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”,列书过多。另一方面又“罣漏太多”,如“把史部书一概屏绝”,而在梁启超看来,“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”[24]。平心而论,虽然胡目有授人以渔的考虑,但从“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”应指点“国学常识”的角度衡量,胡目确实如梁启超所言,过于“主观”,“文不对题”。而胡适本人,也在一定程度上“领受”了这 *** 评。1 *** 5年,胡适在平民中学演讲时提到:“关于要读什么书的一个问题,在《京报》上已经登了许多学者所选定的‘青年必读书’,不过这于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处,因为都是选者依照个人的主观的见解选定的,还不如读青年自己所爱读的书好。”[25]胡适所言“选者”,当然包括他自己。
而梁启超晚年所开国学书目,则专为那些“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”[26]的青年指点“国学常识”而设。在他看来,“国学常识”乃“ *** 常识”的首要内容,是中国青年必须首先了解的。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中有些书的评介已流露着这个意思。比如,梁启超说“前四史”“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,吾辈为常识计,非一读不可”[27]。《更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末尾云其所举“各书,无论学矿,学工程学……皆须一读;若并此未读,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”[28]。《读书法》更是明确说:“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,做 *** 要有做 *** 的常识。晓得本国文献,便是 *** 常识的主要部分。”后来,梁启超应《京报副刊》邀请推荐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,所举皆为中国古籍,此亦可见“国学常识”在其理想的“新民”人格中所占的地位与分量。之所以如此主张,与“欧游”后梁启超“自西向东”的文化转向有关。他亲眼目睹了“科学万能”、 *** 竞争等迷梦破灭后西方社会的人生观及 *** 危机,打破了以往“进步”的西方想象,醒悟到中国古圣先贤的“人生哲学”最值得宝贵,具有恒久价值,不仅可以供我们“终身受用不尽,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”[29]。沿着这样的思路考虑,“国学常识”自然是“ *** 常识”的首要内容。
1 *** 3年4月,因旅居缺书,梁启超先“凭忆想”撰成《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。四五个月后,又在其基础上修订出《读书法》。目前,学界集中关注的是前者,其实,罕见提及的后者因为是晚出的论著体,相对于簿录式的前者,不仅更具逻辑 *** ,而且充分阐述了如此开列的目的、缘由,对诸方面书籍内容、价值的评析及相关研读法的提点也更为周详、 *** ,有些看法甚至有所修正。(当然,后者举书数量略小于前者。)因此,探究梁启超推荐国学书目及其“ *** 常识”观的“晚年定论”,应以后者为准并参考前者和梁氏所撰其他书目及读书指导类著作。
《读书法》供国文科初级使用,专谈本国书,期望指导青年“人人得有国学基本知识”。一开篇,梁启超便联系西风渐盛的时局,提出“为什么读本国书?读本国书有何用处”这个颇为尖锐的问题,并点明这在“从前绝对不成问题,今日却很成问题了”。在他看来,读本国书有如下三种用处:之一,“帮助身心修养及治事的应用”;第二,“知道本国社会过去的变迁情状,作研究现在各种社会问题之基础”;第三,“养成对于本国文学之赏鉴或了解的能力及 *** 练自己之文章技术”。随后诸章便从这三个方面逐一展开,胪举应读的要籍并评述内容、提点读法。这个理路,明显由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的“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”“ *** 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”“韵文书类”“小学书及文法书类”“随意涉览书类”五类删改而来,但更具逻辑 *** 。后者的五类划分,既按阅读的目的、 *** ,也按学科、文体,显然违背了梁启超本人讲解作文法时强调的分类三原则中的“对等”(“所分类 *** 质相等”)和“正确”(“所分类有互排 *** 不相含混”)[30],是故他自嘲道,“所列不伦不类”,“若绳以义例,则笑绝冠缨矣”[31]。《读书法》改为按阅读目的或用处分类阐述,标准更统一,更有逻辑 *** 。
《读书法》因为是论著体,对诸方面书籍内容、价值、读法的评介也更为周详、 *** 。比如,梁启超把关于第二方面的学问称为“文献学”,认为大部分是历史,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“国学”。他具体分为获得常识和从事研究两个层次来谈。他首先强调了前者的必要 *** :“晓得本国文献,便是 *** 常识的主要部分。我们 *** 曾经做过什么事,所做的事留下好的坏的影响给我们的共有多少,这是和我们现在、将来的命运关系最切之问题。我们无论做何种事业,都要看准了这些情形才能应付。”鉴于目前还没有编出好的国学常识书籍,万不得已,他推荐青年阅读:《左传纪事本末》(能读《左传》原文更好);《通鉴纪事本末》(能读《通鉴》原文更好);《宋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;《文献通考》之下列各考(《续通考》《皇朝通考》附):田赋考、钱币考、户口考、职役考、国用考、 *** 考、学校考、职官考、乐考、兵考、刑考、经籍考、四裔考;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之各部各类总叙;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之各省各府总叙。这个书单考虑到了历史事件、典章 *** 、书籍学术、地理沿革等,纵剖横描,可谓周全。不过,梁启超却无奈地指出,这些书卷帙太多,不必要的资料不少,必要的资料却并未齐备。更进一步,他推荐青年读先秦“中国文化初成熟”时代产生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二十八篇等比较可信的元典,因为他们“支配二 *** 的社会心理”。获得国学常识后,若想从事研究,梁启超首先推荐王充《论衡》、刘知幾《史通》、郑樵《通志略》的叙论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,认为“这几部书都是极富于批评精神的”,读之“可以开拓心胸,且生发好些法门”。随后,他提点了如下五种“研究法之普遍原则”:之一,“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”。第二,“用耐烦工夫去搜集资料”。第三,“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”。第四,“用致密技术去整理资料”。第五,“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”。类似原则,梁启超在《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》和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等论著中也有阐述,可以参看。最后,梁启超推荐了一些应用上述原则的典范著作,比如,他荐读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等,提示要“看他们怎样的驾驭资料,且所下判断何等谨慎”。在梁启超看来,清代经师做学问的 *** ,和近代欧、美人研究科学的 *** 略同,“不惟在学术上可以引起种种发明创造”,即就涵养“勇敢、耐烦、明敏、忠实、谦逊”等德 *** 论,亦极有关系,青年应多下些工夫。这种论述,不仅层次分明、环环相扣,而且情理兼到,很有说服力。
《读书法》对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中的一些观点还做了修正,这主要集中在第三方面。后者虽列有“韵文书类”,“随意涉览书类”所荐《世说新语》《定庵文集》等少数书籍也属文学类,但并未推荐小说,也未刻意标举古文,原因是梁启超列举这两类书籍的目的仅是“专资学者课余讽诵、陶写情趣之用,既非为文学专家说法,尤非为治文学史者说法,故不曰文学类,而曰韵文类。文学范围,最少应包含古文(骈散文)及小说。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,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”。至于古文,他认为“本不必别学。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、《左传》《国策》、四史、《通鉴》及其关于思想、关于记载之著作。苟能多读,自能属文,何必格外标举一种,名曰古文耶?故专以文鸣之文集不复录。(其余学问有关系之文集,散见各门。)《文选》及韩、柳、王集聊附见耳。学者如必欲就文求文,无已,则姚鼐之《古文辞类纂》、李兆洛之《骈体文钞》、曾国藩之《经史百家杂钞》可用也”[32]。可见,此时梁启超并不认为文学欣赏和写作的技能是需要刻意培养的“国学常识”。
而在后来所撰《读书法》中,梁启超却将养成文学赏鉴能力、 *** 练文章技术视为“读本国书”的三大目的之一,这固然与预期读者水准略低有关,但更主要的原因是,伴随着撰著成文,他的思考更周密成熟了。梁启超首先从“ *** 常识”的高度立意,反驳一些人所持有的“白话文学通行了,旧书可以不读”论调,阐明阅读以文言为主体的古书之必要 *** :“我们不妨专作白话文,但不能专看白话书。现在留传下来最有价值的书,百分中之九十九是用文言写的。我们最少要有 *** 翻读的能力,才配做 *** 中之智识阶级。即以文学论,文言文自有文言文之美,既属中国人,不容对于几 *** 的好作品一点不能领略……白话 *** 得好的人,大率都是文言文有相当的根柢。”随后,梁启超分为三个目的细论。之一,“对于用本国文字写出来的书籍,能 *** 阅读”,这是更低限的要求。他认为,应“挑选几部不浅不深的古书”精读,“务求一字一句都能了解”,这比学校通行的“什么讲古文讲文法等等机械教育强多了”。首先荐读《汉书》《左传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,此后,“还不自满足,更把《说文段注》一读,知道每个字的来源及异训;把《经传释词》一读,知道古书特别语句之构造法,那么,便可以读先秦古籍和读近人白话文一样的 *** 了”。第二,“为 *** 练自己的文章技术:令自己有什么观察所得或感想所及,能彀极 *** 的发表出来,恰如其分;令别人读去,毫无不了解之处,又不至误会。再进一步,能令读者感动,得着自己所想得的发言效率”。要得着这种技术,先要“找些前人名作来做模范”。鉴于白话文名作“大率属于纯文学的小说类”,不适宜“作初学文章的模范”,他建议多读文言文,因为文言技法也可应用于白话,而且事半功倍。文言文中,他觉得前面推荐的《汉书》《左传》等太古奥了,也不推荐明清以来所谓“古文家”专倡的韩、柳、欧、苏之文,“以为他们浮辞太多,而且格调章法往往故为矫揉,不近自然”,而郑重推荐后汉、魏、晋间之文和前清朴学家之文,认为它们“句法整齐,条理明畅,无浮响,无枝辞,择言必雅而不伤奥涩,蓄意尽达而仍复谨严”。第三,是培养文学的趣味[33],“对于好的文学能彀欣赏”。不外把一般人所公认的名作多看,“心爱的便加讽诵”。除推荐《楚辞》、陶渊明诗等传统诗歌经典外,梁启超还推荐了纳兰词、《桃花扇》《 *** 传》等词曲、小说经典。小说的纳入,使书单更全面了。
此外,《读书法》更能体现梁启超的 *** 见解。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因驳斥胡适书目而起,既纠正了胡目的偏误,也没有摆脱胡目的影响,比如,类目中的“思想史”“小学书及文法书类”即有胡目“思想史之部”“工具之部”的影子。《读书法》则冲破了胡目造成的思维定势,完全按自己的主张结撰,更具 *** *** 。
《读书法》对之一方面关于“身心修养及治事”书籍读法的提点也值得注意,因为它具有不同于“整理国故”主流新派的纠偏价值。梁启超指出,身心修养虽然要遇事磨练,但也须平日用功:除了良师益友提撕督责外,书本上的前言往行也可以鞭辟浸 *** ,给予“很好的 *** 、启发、印证”。本国先辈的嘉言懿行,“读起来格外亲切有味”。此类书“全世界各国怕没有比中国更多的了”,理学家的著述几乎全部都属这类,但是有许多陈陈相因的话。因此,应该先把“虚玄的哲理谈”和“形式的践履谈”(“礼教上虚文”和“外部行为之严谨的检束”)撇开,专看可以切实受用的修养谈。经过精心筛选,梁启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