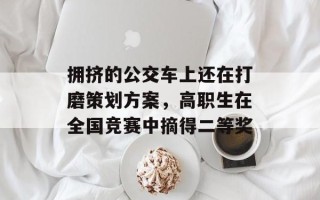中国建筑师刘家琨荣获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(The Pritzker Architect *** e Prize)的消息震撼了建筑、艺术、文化等领域。
普利兹克建筑奖由普利兹克家族于1979年通过其凯悦基金会设立,是被国际公认的建筑界更高荣誉,有着“建筑界的 *** ”之称。刘家琨是该奖项的第54位获得者,也是继王澍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。
而在好友眼中,刘家琨其实是个被建筑“耽误”的作家和艺术家。
1956年出生的他,与那个年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热爱文学。1984年,刘家琨的小说《高地》被收录进《四川文学》。1987年到 *** ,他被借调到巴金文学院从事文学创作。上世纪90年代,刘家琨出版了带有强烈理想主义气质的反乌托邦小说《明月构想》,小说主角就是位建筑师。在他看来,小说和建筑拥有内在的相似 *** ,“都需要虚构一个现实,构造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。”
他还曾正规地学习过绘画,从重庆建筑学院毕业后的十年,他一直想画画,与川渝地区的画家、作家、诗人交往甚密。此番获奖后,何多苓、艾轩在1984年创作的经典油画《第三代人》再次被提及,在这幅描述 *** *** 后新一代知识青年群像的作品中,刘家琨就是模特之一,他站在诗人翟永明(红衣女子)左手边,身着黑色外套、神情肃穆。这幅画在2011年秋季拍卖会中以2875万天价成交,现收藏于上海龙美术馆。
展开全文
油画作品 《第三代人》 1984
刘家琨的建筑作品亦是艺术本身。他擅长将乌托邦与日常生活、历史与现代 *** 、集体主义与个体 *** 等看似对立的元素交织在一起,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建筑,赞颂普通民众的生活。
他以混凝土为墨、旧砖瓦作笔,在城乡褶皱处书写着粗粝的诗意。从 *** 震后 *** 里 *** 的“再生砖”,到成都竹林掩映的“火锅式”西村大院”,再到鹿野苑私立石刻博物馆的禅意叙事,刘家琨用23年实践撕掉“风格”标签,成为中国建筑界最特立独行的“在地叙事者”。
(文里·松阳三庙文化交流中心)
他的设计哲学强调“建筑应揭示地方内在品质”,通过材料、工艺与环境的诚实对话,塑造诗意空间。2008年 *** *** 后,刘家琨认识了 *** 中 *** 的15岁小女孩胡慧姗的父母胡明、刘莉,他们的悲痛和坚强深深地触动着建筑师刘家琨,他很想为这家人做点什么。几番思索后,刘家琨决定为胡慧姗设计纪念馆。
(胡慧姗纪念馆)
这个位于四川安仁建川博物馆的小树林里的建筑,刘家琨摒弃了一切技巧化的设计,以水泥浇筑的 *** 帐篷为原型,采用框架结构及“再生砖”材质,表面施以乡村最常见的抹灰,室内外均采用红砖铺地,室内两侧墙上陈列着胡慧姗短促一生中留下的少许纪念品:照片,书包,笔记本,乳牙,脐带……建筑内外单纯、朴素得跟灾区的情景一样,却又意义非凡,没有任何宏大叙事,只有对所有普通生命的“纪念和尊重”。
走进他的 *** 作“西村大院”,你会惊叹这位在成都土生土长的大咖竟然把建筑变成了一个 “大大的火锅”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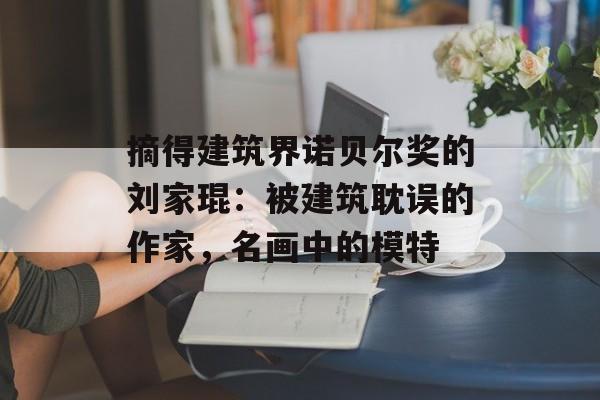
一个巨大的五层环形混凝土回廊包裹着市井烟火,围合出 *** 的院落。竹影在镂空砖墙上游走,屋顶坡道与空中菜园碰撞——这里没有精英主义的孤傲,只有对市井生命的盛大礼赞,这也印证了他的“火锅哲学”,即里边什么都能装,也有很强的包容 *** 。在该项目斩获 *** 建筑师协会金奖时,评委会都惊叹道:“他让建筑学会了呼吸市井空气。”真正的先锋 *** ,或许从来都是从土地深处向上生长。
(西村大院)
谈到设计理念,他认为要“平等地对待建筑、林间空地和竹林”。使用当地的材料,体会当地的生态。正如刘家琨所述“我把林间空地看做明亮的大厅,竹林看做幽暗的大厅,我将这个小建筑切分的更小,然后将其聚拢在一起,就好像一堆石头围出来的建筑。在室内,你还能通过‘石头’和‘石头’之间的缝隙向外看,使内外在视线上流通,充分感受到建筑室内与外部景观的联系。”
(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)
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这段话,你可以走进2002年竣工的四川省之一家私立博物馆——鹿野苑私立石刻博物馆,刘家琨让馆外建筑陈设融合进了 *** 园林意境,采用中国传统园林布局手法,上游有石桥,下游为河湾,野生乔木、河滩卵石与现代 *** 的建筑和传奇 *** 的收藏相映成趣,展现“野逸幽深”的自然美学。
(刘家琨主持的“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 ”)
与自然共生,是先人所遗留下来的深刻哲学,亦是东方人理所当然的状态。在做建筑周边景观时,刘家琨认为:“本来那儿就有树,不要砍它,绕一绕、躲一躲那些已经有的树。那些竹林本来就有,所以没砍,在现场躲开这个躲开那个,躲一躲自然就会偏一偏。鹿野苑景观设计的思想就是不砍树,挺好的地方,就不砍树。”这种对自然痕迹的保留与敬畏,是渗入呼吸的生活本能,亦是东方智慧在 *** 沉淀中形成的生命自觉。
(建川博物馆聚落-钟博物馆)
从灾后重建到城市更新,刘家琨始终行走在“民间智慧与当代 *** ”的钢丝上。当被问及如何定义自己的建筑时,这位拒绝扎哈式炫技的实干家笑言:“不过是给土地写注脚的人。” 一切正如日本建筑 *** 隈研吾对他如此评价:“他握住了中国土地的指纹。”